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采访、撰文:若士,编辑:程絮圆,本文为对作家唐诺的访谈节选。
纸质书的未来在哪里?现在又有多少人跑一趟实体书店只为了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热爱文学和阅读的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实体书成为一种历史,完整而认真的阅读成为一种奢望?
本期单读节选了对作家唐诺的访谈,他与我们分享了他对出版业的看法,尽管出版业的萎缩是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但是文字本身的力量,依旧是无法被其他媒体形式所替代的。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 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共组著名文学团体“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2013 年出版散文力作《尽头》,探索极限和人的现实处境,获评《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与台湾金鼎奖。
我们的文学读者正在不断地流失
单读:您曾经在 2010 年香港书展上做过一个演讲,《书——2000 本的奇迹》,当时那篇文字发表在《单向街》第二期。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讨论出版业的衰落,您作为一个资深的编辑,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中有一句话,大致是说,美好的东西通常都很脆弱,但它不会消失,书就是这么一个动人的奇迹。前些天我在《收获》上看到您的文章,又讲到出版业,讲到读者的流失,似乎是更惨淡更悲观了。
唐诺:这个如果在大陆讲的话,可能会有点犹豫,因为大陆出版业看起来并没有明确的衰退——起码从数字来看是这样,甚至有人认为出版业比以前更蓬勃。但是我大概有一个判断:比较认真的文学圈子还是会缓缓萎缩,会比较倾向于——也许是不太准确的词——倾向于往通俗的方向走。
台湾的情况非常严重,台湾的两千本已经消失了。当时我讲的是,两千本是出版的一个生死线,两千往下,这本书就要赔钱。靠着某些出版者、编辑的善意,他们认为这个书还是应该要做,但是就必须要出其他某些书,才能够 cover。现在这个“两千本”,消退到五百到一千本,所以台湾出版目前的状况,连崩解都谈不上,因为崩解好像太辉煌了,事实上是缓缓地下滑,像灯在缓缓地熄灭一样。

2013-2017 年,台湾出版机构与出版图书的数量
台湾出版业一直在比较困难的状况底下工作,因为它先天的 base 比较小,两千万出头的人口,在这里头产生一批读者。从某个程度讲,台湾的出版业是很精明的,他们必须懂得用最节省的方式——哪边的成本可以省,哪边可以多出一点点收益,怎么行销,想办法找到生存的可能。这方面的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但是总归来讲,一个大的问题是读者不断在流失。我说的读者是所谓的文学读者。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状态,只是严重的程度不一样,因为每个社会有它不同的力量在左右。一个社会刚刚富裕起来的时候,它会比较有余裕,充满好奇,甚至愿意去尝试。我们经历过那些时间,大陆也经历过这段时间。我们童年的时候要买一本书都是大事情,有的时候书都找不到。现在来讲,台湾是好书供应过度——相对读者来说,好书印太多。尤其是享乐的发生,游戏时代的来临,文字的大量遗忘……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时间很短,没有纵深,没有传统的束缚,抵抗力很弱,基本上就是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

那大陆,我想这个状况无疑会延迟。原来起步就比较慢,改革开放富裕起来之后,大家可以读书、买书。上一代的人买书都是事情,但是这一代,只有你爱不爱看。在这个情况之下,它会有一段较蓬勃的时间。
包括在文学世界的待遇,大陆作家目前可能是全世界经济上收益最稳定的。日本老早垮了,台湾也是。在很多社会书写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养活你的,你要做别的事来养活自己。比方走进影视圈。在美国就往好莱坞挤,一进账,你的收益就会完全改变,你会变成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人。那样你可能就会离开我们所谓“文学书写”的世界。
那个世界是一个很清冷的世界,最好是不要进去
单读:您说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都是因为出版市场、文学市场无法支撑了吗?
唐诺:对,有很多原因,并且它们互为因果,但是最终的一个背景,就是读者流失,读者不在了,而且他们可能不会回来。我当初的分析是,读者有同心圆状的三层,核心是正确的读者,占数比较小,一代一代都差不多,不会有戏剧性的变化。毕竟总有些喜欢文学的人,在有的年代,甚至为了走这条路要跟家里对抗。这部分读者的稳定性是较高的。最外层是错误的读者,他们现在慢慢不会发声了。过去他们在什么情形之下发声?大约是一个浪潮起来的时候,某一个社会议题,你不看就不知道人家在谈什么,所以要去看书。
过去我作为一个出版编辑,最争取的是中间那层,假装的读者。他们其实能力没有真正到这个地步,甚至阅读是吃力的,可是他们有一种向往,或是受到某种诱引,不管那是误会还是启发。这一批读者某些会离开,因为假的东西撑不久,但撑久了就会变成真的。所以读者才会成长。

其实大半核心的读者,都经历了这个阶段。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在假装。比方你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或者你这样做的话,你看重的那些人会喜欢你,你会慢慢进到这个世界。我用过孟子的话,他讲五霸是假的,可是他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假久了变不回来,就是真的,后来你也不会知道它原来是假的。原来这批读者是假的,可是假装的读者最受社会变动、某些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
比方说,过去我们认为阅读这样的书、知道这些事情是一个虚荣的事,你会在异性面前更有魅力。现在没有人理会这个事,你如果会唱歌、会跳舞可能更受欢迎。所以假装的读者最快流失、几乎不见,尤其在台湾。大家不用再装了,因为那个世界是一个很清冷的世界,最好是不要进去。
读者大量流失之后,只剩下核心的读者。那两千本中,核心可能本来就是五百左右,所以目前台湾大概就暴露了这个真相。出版数字的变动,从四千掉到三千,是出版社的收益在锐减,从两千掉到一千,是一个临界点,就是成本。这是不容易移动的,因为有所谓的价格铁律在里面,比方纸张的价格、印刷的价格、工作人员的薪水。比较能够变动的是作者的待遇,所以现在作者的待遇又往下调了。现在台湾出版社的经营很辛苦。
拿了一根绳子干吗报官?绳子另外一边牵着他们家的牛。
单读:您在文章里面还讲到了一点,今天很多有文学才能的人,尤其是现实主义那一派的,很多都在做电影电视。我去年看那部法国电影,《她》,伊莎贝尔·于佩尔演的,她原来在出版社工作,后来开了游戏公司,她的前夫是个作家,也想去写游戏。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转变。影视、游戏越来越占据文化生活的中心,很多也做得很好,跟它们相比,文字、文学不能取代的是什么呢?

电影《她》海报
唐诺:通俗的世界,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看卡尔维诺曾经为费里尼《虚构的笔记本》写过一个序,非常精彩。在费里尼那个年代,包括像德·西卡这些人,是意大利电影很伟大的时刻。费里尼不用讲,德·西卡的《单车失窃记》(《偷自行车的人》 )、《昨日,今日,明日》,都是非常厉害的电影。
有趣的是,卡尔维诺讲,我尊敬他们,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喜欢过他们。他自己大量看的是好莱坞的电影。大概因此他就把电影归为比较适合享乐的媒体。吓我们一跳啊,总觉得他这个选择让我们有点惊讶。但我是懂的。
当然我对电影有我的——可能是一个偏见。你如果习惯用文字、文学来表达,我会去问你一个问题,一部电影能够负载多少?因为朱天文是编剧,现在我的儿子谢海盟也是侯孝贤的编剧。侯孝贤的东西我也会探探头,看一看,问一问,甚至有时说两句话。我们的结论大概是说,像侯孝贤这样一部电影能够负荷承载的,大概相当一个短篇小说的幅度,不能更多。这很清楚,作为编剧,即使你剧本写得更丰厚,最后侯孝贤会说剪不进去,因为毕竟电影有一个规格,那就是它能承载的长度和广度的可能性。

卡尔维诺
另外一个是深度的问题,这牵涉到文字载体和影像载体的不同。我经常说,影像载体不是刚刚发生的,人类是从影像载体开始的,文字是后来才发明出来的。人类跟影像相处了几百万年,跟文字的相处不超过一万年。而且文字的发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奇迹,因为当初在地球上的社群——从二三十个人到两三千人,我们现在称为部落也好、社群也好——粗略估计只有 5%的人类发展出文字,西亚发生了,中国发生了,印度发生了,埃及发生了——那埃及文字是不是受到西亚楔形文字的影响,这个我们就不再去探讨——大约的估计是 5%。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在文字的涵盖范围之内。
为什么发展出文字?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它并不理所当然。没有办法讲得很仔细,稍稍多讲一点,就是为什么发展文字?
影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会直接看到它。它变得非常可信,黑是黑,白是白。后来慢慢发现说,我们的眼睛会不会欺骗我们?我们的可见光只有一小节,我们的眼睛究竟是不是可靠的?这当然是比较麻烦的问题,甚至牵涉到认识论的问题,比方说你眼睛看到的绿色和我眼睛看到的绿色是同样的绿色吗?先不谈这些,影像的好处,是基本上有一个全景。你比较一下四格漫画就知道了。每一个图像所占领的范围较宽,间隔较大,原来是诗衔接了这个东西,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连接发生在你的内在。所以书写不是从散文开始,而是从诗开始。而且当时因为书写的成本很高,文字是非常简约的。所以大部分的记忆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而不是在载体上头。

《茉莉花图》,南宋博物绘画
可是我们慢慢会认识,用卡尔维诺的话讲,我们的认识不断在细分。我们慢慢分辨出来,树不是只有树,有松柏,各种,你要细腻地去分。图像很难再做进一步细腻的分割,而且会变得很麻烦。
早期生物学在华莱士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所有的生物学者都是好的画家。他们必须要细致地,把叶片、花须、根部、大小画得仔仔细细。原来造字也碰到这个问题。比方最早“木”就是一个树的样子。可是后来我们必须要分割各种植物,因为这跟我们的生存有关,我们要知道它是松树还是柏树。当时造字很困难,所以走了不一样的方向。除了中国文字以外,其他都走向拼音。所谓拼音就是说,我放弃图像,而用声音来记录。因为命名已经跟人类相处了两三百万年,而且命名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当下决定叫它什么,大家同意就过。中国最后是形声字的出现,保留了形象,但也是用声音来分辨,这告诉我们什么?视觉无法再做精密的分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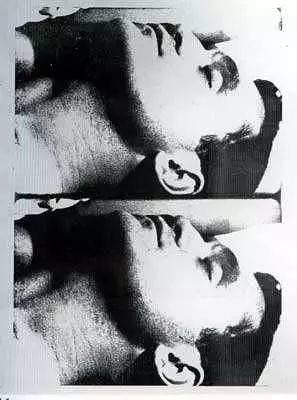
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沉睡》
视觉还有一个大的麻烦,就是人面对非具像、非具体存在的东西的时候。比方说“梦”,你的视觉就是一个人在睡觉。全世界最无聊的一部电影,就是拍了 8 个小时一个男人在睡觉——他做梦我们是不知道的。
中国造这个“梦”字很有趣,它是一个人躺着,可是眼睛是睁开的,好像人睡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东西,但是也只能用会意来传达。你真正要进到某些价值、某些思维的时候,怎么表达?所以电影只能采取接近原来诗的方式,隐喻的方式,我把两个场景的东西收在一起,然后尽在不言中。但是以隐喻的方式接触到内在,跟你真正写进去是不一样的,它的厚度、稠密度跟深度毕竟不同。
简单讲就是文字慢慢填满了人认知的很多空隙,它更稠密,是一个能够深化的载体。从文字退回影像,只能说人类累了,他甚至想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不想知道。他的好奇消失了,他的某些部分停止了。所以即使影像有非常大的进步,解析度更高,更方便,每个人的手机都能够拍出当年只有西德的光学才能够做到的影像效果,它仍然是影像,仍然不是文字,依然是受限于影像的承载力,它毕竟是视觉的。可是人的感官是很复杂的,我们有听觉、有嗅觉,有味觉、有触觉,有各种感觉,甚至是更内在的体会。

《文字的故事》,著:唐诺,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所以怎么样讲?我在《文字的故事》里头讲,人类从没有文字走到文字,要弃绝文字也没有什么可惜。文字不过是一堆符号,不过是一堆线条。有一个笑话,你怎么被人家抓了?因为我拿了一根绳子。拿了一根绳子干吗报官?绳子另外一边牵着他们家的牛。文字是这条绳子,这条绳子丢掉并不可惜,问题是那头牛跑掉了。有某些更深层的东西必须要仰赖文字。人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个比文字更适合负载这些东西的载体?你要问我,我会说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采访、撰文:若士,编辑:程絮圆。